研究所
聯系方式
兩名義烏商人的突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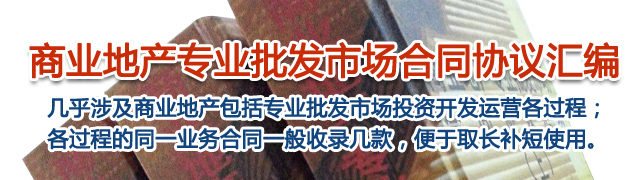 |
 |
中國制造已經不能再被視為一個整體。中國制造自身已經在分化和變遷。其中存在著大量的代工公司,它們依賴于訂單,沒有自己的品牌,單純的外貿。但其中也有像新光和浪莎這樣的公司,它們已經意識到了品牌的重要性;它們在頑強地建立自己的渠道,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它們一步一步向制造業價值鏈的高端挪動;它們也都意識到了資本的重要性,因為它們都不甘心局限在利潤微薄的加工業,或者說,它們不甘心自己始終存在被資金繩索勒到窒息的危險 。
一
四層樓的義烏國際商貿城。它并不擁擠,出乎意料的干凈、整潔。所有描述義烏的文章中都會出現這座擁有大約6萬家店鋪的國際商貿城。其中一個最經典的描述是,如果你每家都轉上3分鐘,一天8個小時不停歇,那么,你要用一年時間才能從它里面走出來。
它不是我們印象中那種人山人海的批發市場。賣家們并不殷勤。看守店鋪的大都是雇來的年輕女孩,她們首先學會的是如何分辨觀光客和真正的買家。所有那些詢問商品零售價格的人可能都不被算作真正的買家。以一個印制著素雅圖案的布制包為例,只有在400個以上才會考慮出售。
這座小城距離上海300公里。從最近的杭州蕭山機場趕來,也要將近兩個小時。但是在過去的不到三十年時間中,它卻成為世界的超級市場。人們用各種奇妙的語言來描述它,比如,“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卻幾乎什么都有”;再比如,它被稱作是小商人們的“應許之地”或者圣地麥加。它自己的口號是“商品的海洋,購物者的天堂”。有超過60%的義烏市民擁有工商營業執照,義烏工商學院的副院長賈少華說,“它的人均銀行存款和汽車擁有量可能是全中國最高的”。
不過,它并不僅僅是一座貿易之城,盡管在義烏,人們信奉 “無商不富”。世界超級市場的巨大貨流量,同時也像傳送帶一樣,帶動著本地制造業的發展。在義烏國際商貿城6萬家攤位背后,有將近3萬家的制造企業。他們出售自己的產品,同時也為國際品牌代工,其中的佼佼者則擁有了自己的品牌。一家吸管制造商生產著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吸管,一家拉鏈生產商每年生產的拉鏈可以繞赤道轉200圈,一家襪子生產商還破天荒地成為了北京奧運會的贊助商。
如果你是這些商人中的一員,在義烏國際商貿城擁有一個攤位,或者更進一步,同時還經營著一家生產襪子、螺絲刀、手杖或者箱包的工廠,那么,不需要懂得次級貸款以及華爾街的各種把戲,你就能明白現在它意味著什么。所有關于這些后果的描述都是一個套路,首先是出口量的下降,接著你發現自己的現金流出現了問題,因為客戶不能及時付賬,再接下來,如果不多加小心,你自己也會陷入困境。世界不再迷人,也跟你年輕時候不一樣了。
四處是危言聳聽的流言,不斷有公司解散清算的消息傳來。大部分人都戰戰兢兢。惟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信心宣稱自己能夠化險為夷,盡管這種信心有些時候也不是那么確切。很多時候,他們的言語更像是安慰別人也安慰自己的心靈雞湯。這些言詞并不提供及時的行動指南,但總是被需要。
二
出租車駛出義烏城區,性急的司機不需下車,在作為出城登記點的房屋門口大喊一聲:“新光。”那些密布著制造工廠的工業園分布在城區之外,出于治安考慮,每輛駛出城區的出租車,都要在出城登記處登記。
新光飾品的創始人周曉光可能是義烏最著名的商人了。她是義烏市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她頻繁出現在電視和報紙上。在見我之后,她還要接受王小丫的采訪。后者是一名電視節目主持人,要為中央電視臺制作一檔報道“兩會”的電視節目。
1995年,周曉光和她的丈夫虞云新創辦了新光飾品。她沒有接受過太多教育,面對外界時總是出言謹慎。但是她和自己的公司卻在義烏眾多的飾品公司中存活下來,而且成為最強者。在他們成立公司時,義烏已經有100多家飾品公司,最高峰時一度接近4000家,隨后這個數字隨著行業大環境的變化而變化,“2008年3月份的時候有3000多家公司,2008年年底,有2000家左右,這么短的時間,三分之一的公司就沒有了。”周曉光說。
她剛剛滿46歲,穿著一身黑色套裝,扎一條素花紋的絲巾,仔細描了眉,短發被挑染過,說話時臉上表情波瀾不驚,神情鎮定到漠然,既平靜又認真。
她坦率地承認自己的公司并不是一個龐然大物般的商業組織,盡管在這個小城它已經是如此形象。托馬斯·曼在一部描寫小鎮商人的小說中說,再小的城市也有自己的愷撒。在義烏眾多以微不足道的商品作為生產對象的公司中——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這里的公司選擇吸管、拉鏈、打火機和襪子作為主業——年銷售額接近30億元、總資產50億元的新光正扮演著小城愷撒的角色。
一篇2008年年底的報道引用中國飾品協會的說法,已經有將近30%的飾品企業由于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和金融危機影響而倒閉、停產。這個行業內的領先者新光,在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間以50%、50%和30%的速度增長著。但在已經過去的2008年,這個數字為15%。不過這已經讓周曉光滿意。她不斷慶幸著自己在2005年就開始的戰略調整。
這次已經被眾多媒體報道過的轉型,起源于周曉光對海外市場的考察。當時,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涌入飾品行業,無論是在制造端還是在銷售端。國內制造商生產的產品不是已經出售一空,就是被大量積壓在銷售商手上。這讓周曉光提前嗅到了市場上漂浮的焦躁氣息。盡管飾品制造商在當時還過著舒服日子,但是周曉光仍然決定,新光要逐步“從批發商轉向零售商,要從制造商轉型品牌運營商”。與這兩個決定相關的是: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以及塑造自己的品牌。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決定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形容都不為過。品牌讓這家公司可以避免淪為單純的代工企業、受制于海外市場的訂單。除了幾家代工企業中的巨無霸之外,這類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中不堪一擊。直接掌握渠道則讓周曉光和新光對市場需求的反應更加敏捷。新光的董事長助理徐平甚至認為,很多時候,不是因為沒有市場需求,而是缺失了銷售商環節,導致了很多中國代工企業的倒掉,因為很多訂單正是由渠道傳來的。當渠道商自身面臨困難時,訂單也就消失了。
對市場的敏銳同樣讓周曉光較早地覺察到了經濟蕭條對飾品行業的影響。2008年4月,周曉光在美國拜訪當地的客戶和朋友,順便做市場調查。她隨機走訪了紐約第五大道的幾家飾品店,結果發現,這些店的每天客流量從100人下降到40人,人均消費金額從200美元下降到80美元,自然而然,每天的銷售額也銳減。她知道,風向又一次變了。
后來她說,這讓她在面對2008年8月和9月份開始的壞形勢時,內心平靜,而不像很多民營企業家那樣驚恐萬分。那些一直搭乘經濟快車的企業家們,往往認為公司的高速成長是理所當然之事。
2008年年底,周曉光跟義烏市的很多企業家做了交流。她安慰大家說,事情并不是真的像所有人都認為的那般艱難,已經看不到陽光和希望,“而是大家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一下子覺得很恐慌”。恐慌之后,接下來,你就會迷失方向,不知道目標是什么,對未來和不確定性的模糊認知,又進一步增加了今日的恐懼。
盡管如此,毫無疑問,周曉光看到的未來也并不是陽光燦爛的大道。周曉光對新光高管團隊說,2009年只要保持2008年的業績即可。只是她希望,這段歲月能變成一個沉靜時期。公司在沉靜時期能夠安心完善自身。這種完善在高速成長時期往往讓人難以顧及,畢竟,在高速成長時期,成長才是第一位的。只要印鈔機能照常工作,沒有人在乎工廠建在哪里。
三
翁榮弟西裝革履,系著一條紅色條紋領帶,梳小分頭,說話時滿臉堆笑,完全符合大眾對浙江商人的想象:低調、不時打哈哈,無論是眼神還是面部表情都傳遞出精明商人的感覺,說話時聲調會隨著談話內容的變化而變化——當他壓低聲音時,他想表明,我在抱怨,我有不滿,但是你知道就行,可別跟別人說。他的公司在緊急地大量招聘工人,數字高達3000,而翁榮弟認為,這個數字仍然難以滿足浪莎的擴產需求。一則新聞報道說,甚至在春節期間,浪莎也沒有停止生產,數千名工人放棄了假期。
他住在杭州一家星級酒店內的標準間,因為周末他要在浙江大學學金融。從傳統制造業起家的商人們發現金融業才處在整個經濟河流的上游地位,紛紛表現出對金融業的強烈興趣。比如從飼料業起家的劉永好,如今就是一位金融大亨。
1995年10月,翁家三兄弟創辦了浪莎襪業。和眾多義烏的制造商一樣,翁氏三兄弟也是以貿易起家。后來的報道中經常提到,早年翁榮弟是如何睡在硬座車廂的座位底下,南下廣州,從自己拿到總代理權的廠商手中取貨的。
通過做品牌襪的代理商,建立起全國的銷售渠道,此中的經驗對翁氏兄弟1995年創建浪莎襪業或許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翁榮弟更喜歡說的不是經驗,而是品牌。他總是說,三兄弟當年選擇做襪子,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發現,“西裝、女裝、襯衫、褲子、領帶等都有了名牌,只有襪子還沒有名牌。”創業之前,三兄弟專門到北京注冊了“浪莎”品牌,并且將42大類商標全都注冊上。
1996年浪莎就開始到中央電視臺做廣告。這甚至讓中央電視臺廣告部的工作人員都頗為驚訝:“幾塊錢一雙的襪子,還做什么廣告?”三兄弟的品牌意識之強烈在當時的中國商人中絕對屬于鳳毛麟角。“說句難聽點的,我的利潤幾乎全都投到品牌塑造上面了……(品牌塑造)這個講一講很容易,做起來很難。畢竟拿出去的都是現金。”翁榮弟說。隨后,浪莎又把自己的品牌外溢到了其他紡織品領域,最著名的是浪莎內衣。
接下來,像所有有雄心的中國制造商一樣,浪莎開始頑強地向價值鏈的上端移動。其中最著名的事件當屬浪莎拒絕沃爾瑪訂單引發的風波。在全世界范圍內,沃爾瑪都因為對制造端的不斷壓榨而聲名不佳。盡管這家廉價超市在消費者中擁有極佳口碑,但在供貨商眼中的形象卻截然相反。它總是通過壓低采購價格來迫使制造商不斷降低成本。它讓全世界范圍內的供貨商都戰戰兢兢。一方面供貨商們為不斷地低價、低價、低價而苦惱,另一方面,沃爾瑪的巨大出貨量又讓供貨商們像老煙鬼一樣欲罷不能。
2003年,浪莎進入沃爾瑪的全球采購體系。2005年,浪莎接到沃爾瑪300萬美元訂單,2006年是250萬美元,2007年是220萬美元。但是翁氏兄弟對此并不滿意。2007年7月,翁榮弟表示,除非沃爾瑪提高至少30%的價格,否則浪莎將不再向沃爾瑪提供產品。
翁榮弟后來解釋說,浪莎的舉動并不是針對沃爾瑪,而是針對浪莎的全球采購商。“中國五年以前都不穿尼龍襪了。你拿過來的訂單是尼龍的,那么低端的產品,我的工人工資、原材料成本都上漲,一算成本,肯定做不了。這不是針對沃爾瑪,是針對全球采購商的。和我們自己公司的定位也有關”,“浪莎向所有國內外客戶提出了提高單價的要求,其他的客戶都答應了,就沃爾瑪中國區不接受,我們考慮再三,拒絕了他們的訂單”。
這個故事有個理想的結尾。沃爾瑪和浪莎的合作在2007年年底重新恢復。浪莎沒有失去訂單,但又以強勢的姿態讓自己在制造業的價值鏈上向前挪動了一步。如果一家公司連沃爾瑪都敢于拒絕,那么它沒有任何理由再為了訂單屈服。此后,翁榮弟一直為浪莎的討價還價能力自豪。他認為,這家義烏公司終于有了議價權,甚至定價權,“我們可以把成本算給我們的客戶,告訴他們我們必須提價”。
在另一方面,翁氏兄弟的資本意識來得也格外的早。翁榮弟在數個場合重復過,浪莎從1998年就開始謀求公開上市。可惜這一過程顯得格外漫長,大概十年之后,2007年,通過用7000萬收購原ST長控的控股權,浪莎才實現了借殼上市。而且,這還不是個令人愉悅的開始。只要翻檢當時的新聞報道,就能看出,背后被操縱的股價讓一直做實業的翁氏兄弟頗為無奈。
除此之外,翁氏兄弟還是小額貸款的主發起人,翁榮弟也是金華商業銀行的董事。
四
周曉光和翁榮弟看上去毫無共同之處。
所有見過周曉光的人都對她的好學若饑印象深刻。她總是在不斷提及她在商學院的同學和朋友們。這幾乎成了她最主要的圈子,她將之稱為“外面的人”,其中包括了很多中國最精明的商人和投資家,比如做投資的趙炳賢,還有神州數碼的郭為、康佳的侯松容、格力空調的董明珠、復星的郭廣昌、伊利的潘剛,等等。
她是個商學院同學聚會的熱心組織者,2008年她就組織了兩次聚會,一次在義烏的新光集團,另外一次在杭州的西湖。后一次為的是討論當前的經濟形勢。她會和她的同學們討論自己遇到的各種商業問題,從他們那兒得到各種建議。“我們同學聚會比跟咨詢公司開會還專業,而且同咨詢公司之間是利益關系,同學之間完全是熱心和友善。”
在做出重大決定之前,她都會隨手操起電話,打給自己的某位同學,征詢其意見。在趙炳賢的影響下,她也成了沃倫·巴菲特的忠實信徒。她購買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票,會在每年的5月份去參加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年會。她對金融的興趣也在萌生。到沃頓商學院拜訪時,她提出希望能上一門關于私募股權投資的課。
她謹小慎微,但是把自己向外部世界完全開放。
翁榮弟顯得更加自信。他和自己的兄弟白手起家創建了一家號稱中國襪業之王的公司。成功帶給他信心。但他仍然低調、節儉、謹言慎行。他聲稱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公司內部,白天同客戶開會,晚上則去工廠看機器看工人。他沒有選擇到某個知名的商學院讀書——這意味著進入一個商人社交網絡。他的學習方式更多的來自于自己的實踐,learningbydoing。
如果一定要尋找他們的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公司——新光和浪莎——都倔強地挺立著。中國制造已經不能再被視為一個整體。中國制造自身已經在分化和變遷。其中存在著大量的代工公司,它們依賴于訂單,沒有自己的品牌,單純的外貿。但其中也有像新光和浪莎這樣的公司,它們已經意識到了品牌的重要性;它們在頑強地建立自己的渠道,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它們一步一步向制造業價值鏈的高端挪動;它們也都意識到了資本的重要性,因為它們都不甘心局限在利潤微薄的加工業,或者說,它們不甘心自己始終存在被資金繩索勒到窒息的危險。
除此之外,更加老生常談的是,它們都堅守著自己的主業,而在對外投資時卻謹慎小心。它們一度都沒有經受住誘惑,都曾經參與了多元化淘金游戲,但無論是幸運還是敏感,它們都及時停了下來。“資金充足,而且主業明晰”,周曉光和翁榮弟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不斷提及這句話。
這真不是什么新發現。《基業長青》和《從優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說,每次當他在商學院的課堂上重復說,堅守主業非常重要,除了少數幾家公司之外,鮮見多元化的成功例子,商學院的學生們總是表示出適度的不耐煩:是的,可是這不是常識嗎?而當他講給一些公司的高級經理人時,對方往往會非常動容:是的,你說的太對了,我們對此也有深刻體會。
這兩位義烏商人身上體現的常識是:
1.注重品牌建設,并且為此不惜重金;
2.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把渠道控制在自己手中,這樣可以避免對銷售商的依賴;
3.堅守主業,謹慎投資,克制自己的欲望,抗拒多元化的誘惑。
當然,他們認為自己和自己的公司身上還有更多東西,比如注重研發、特有的謹慎和節儉、對市場的敏銳等。他們同記者的對話或許能更全面地反映出他們對此次危機的觀點,以及他們自己的世界觀。下面是我們談話的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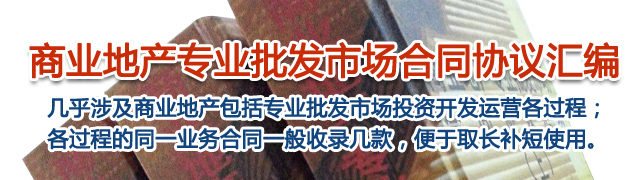 |
 |

